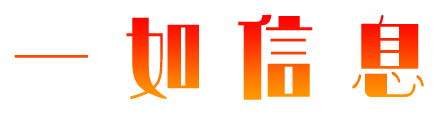【金融政策评析】美国升息遇到瓶颈
最新信息
【金融政策评析】美国升息遇到瓶颈
2022-10-27 12:19:00
美联储这轮货币紧缩政策远未大功告成。美国通胀自2021年3月超过2%的政策目标后,已经连续20个月走高,并在今年6月达到9.1%的高峰,此后仅有小幅下降。面对通胀顽疾,不久前,美联储向市场发出了最强持续加息信号,使此前对联储治理通胀决心仍抱幻想的市场终于有所醒悟。目前,市场对联邦基准利率的平均预期已从6月的3.4%提高到了4.9%。这意味着,在2022年剩余的时间里,美联储有望再加息至少125个基点,而明年初还有继续加息的空间。
疫情后经济刺激下的需求增加、源于地缘冲突的大宗商品价格上升、疫情管控下全球供应链中断是本轮通胀的主要原因。然而,紧缩的货币政策基本无力影响后两个因素。在地缘政治冲突旷日持久,全球供应链调整尚需时日的情况下,美联储的紧缩政策,不得不在抑制需求方面承受重中之重。
值得注意的是,美联储加息的步伐似乎已碰到了瓶颈。美元作为交换中介(交易)和价值贮藏(投融资)的双重功能,以及作为国内货币政策标的与国际储备和结算货币的双重角色,正使美联储的政策空间在今天被空前的压缩。由于金融市场的发展,美联储在试图对实体经济施加影响时,不得不考虑随之而来的金融市场稳定性问题;而在应对国内经济周期的同时,也不得不顾及对全球其他经济体的影响。考虑到美国货币政策的溢出和溢进效应,以及这些效应的相互作用,事实上,在过去30年里,美联储并未有过针对某一政策目标而义无反顾的决策环境。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格林斯潘看跌期权(GreenspanPut),2008-2009年金融危机时的伯南克看跌期权(BernankePut),以及后来的耶伦看跌期权(YellenPut),都是美联储政策归宿的明证。这里,所谓看跌期权是借用金融术语,利用看跌期权在金融资产下跌时赢利的特性,来形容联储的政策本质。更直白地说,这些政策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在实现政策目标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地顾及金融市场的过度反应(下跌),以及国际经济的现实环境。
相比之前的升息周期,本轮的升息或许让美联储更加进退维谷。眼下,从美国内部来看,一边是过热和韧性十足的国内实体经济;另一边则是长期超低利率下催生出的市值过高的金融资产。从全球经济来看,一边是处于相对强劲的美国经济;另一边则是脆弱的欧洲经济和放缓的其他地区经济。针对前者引发的通货膨胀,美联储必须果断出手,把通胀抑制在低位;但如果美国利率上升过快且幅度过大,则可能引发国内金融市场动荡,甚至触发国际金融危机。1980年初的升息,引发了拉丁美洲债务危机;1994年的升息,导致了1997年的亚洲经济危机和随后的俄债危机。如果不出意外,在这一轮抑制通胀的政策博弈中,鲍威尔看跌期权可能要呼之欲出了。
金融市场空前发展
美国战后大约发生过六次显著的通货膨胀,类似本轮这样高通胀率的情景发生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但与上次不同,过去四十年,美国资本市场伴随经济的成长,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发展。1980年,美国股市的资本化规模不到GDP的50%,而2020年已高达GDP的194%,按美元计算增长了27 倍。与此同时,美国债券市场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仅以国债为例,美国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从1980年的31.3%上升到了2022年上半年的121.07%,为 28倍。过去四十年,国际贸易的增长加大了对美元的需求。据WTO的数据,全球2020年的贸易总额为1980年的5.1 倍,其中,约一半用美元结算。在跨国资本流动方面,仅仅在过去十年,外国投资人持有的美国金融资产就从44500亿美元增加到65364亿美元,增幅达47%。
这段时间,美元虽在国际贸易和跨境资本流动中的比重有所下降,但仍然占据着最主要的地位。目前,美元约占世界官方储备货币的60%,占国际贸易结算约50%。在跨境贷款和跨境金融证券中,美元至少占40%。在外汇交易中,近90%以美元结算。即便是通过SWIFT系统的支付,美元的比重也有40%之多。
不仅在规模上,金融市场的深化也加大了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渗透。金融市场中不断涌现的金融创新,使投资人拥有了更多收益增厚和风险管理的手段,也使融资人获得了更加低廉的多元化的资金。金融产品甚至可以帮助投资人实现风险转化、风险分割和风险重组。随着互联网技术,特别是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出现,金融在不断扩大自己的疆域,并且下沉到之前从未触及到的客户群体。金融的这些发展,从某种意义上拉动了广义利差交易的各种机会和杠杆使用的各种形式。在货币政策发生(突然)变化时,根据原来政策(如超低利率)环境,按照当时投资参数设计的各种金融交易和金融运作,骤然间便可能暴露在巨大的风险之中。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愈加复杂
高度发育的金融市场,至少从三个方面改变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并影响到其决策的空间。首先,金融市场的存在使资产变动和融资效率提升,并使其多元化;同时,金融市场赋予了资产和负债的市值属性,从而改变了经济实体的资产负债结构。比如,债券融资的比重增加,而股票增发会快速改善资产负债比率。通过资产负债结构,货币政策继而传导到经济实体的损益和现金流当中。之前联储的利率调整,会通过经济实体融资成本的变化对公司的经济活动施加影响,而在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面前,仅仅“盯市”就会直接改变公司的财务状况。比如,货币收缩政策可能导致负债市值下跌。此外,还可能导致用于激励员工的股票期权等金融资产的价值发生变化。由于升息,债券市值下跌,通过对自身发行债券的低价赎回,发行人会产生投资收益,从而抵消升息对实体的影响。
升息还可能直接影响到公司的融资活动,特别是用金融资产作质押的融资。当利率上升,这些资产市值发生下跌时,贷款机构会要求借款人补充质押品,否则质押品将被减仓以用来还债,但减仓又会导致质押品市值的进一步缩水,引发更大规模的减仓,形成恶性循环,最终打击经济实体的经营活动。那些使用金融衍生品对冲经营风险的实体,升息往往会使对冲出现错位,产生新的风险敞口。此外,依赖直接融资的经济实体会发现,在利率攀升的环境下,发行人二级市场上股债流动性可能锐减,发行市场对发行人甚至完全关闭。2009年,美国雷曼兄弟垮台,很大原因是市场对其执行交易协议能力产生置疑,致使信用风险迅速转化成流动性危机。
其次,美联储货币政策会通过财富效应对实体经济发生影响。根据欧洲央行2015年的一份报告,美国2008年次贷危机期间,住房价格和金融资产价格每下降10%,家庭消费支出便分别下降0.56%和0.9%。而当年美国标普股指从高峰下跌了51.9%,全国住房指数下降了32%。事实上,2008年美国家庭损失的财富(13.6万亿美元)超过了因失业损失的可支配收入(11万亿美元),财富效应对经济的影响甚至从“助攻”转成为“主攻”。
这种财富效应在本轮紧缩中还在强化。据美联储统计,美国家庭及非盈利组织持有的金融资产,从1980年底的7.36万亿美元上升到2021年底117.9万亿美元,四十一年间增加了15倍。同一时期,非金融资产和金融资产的比例则从0.6:1.0下降到0.43:1.0.与此同时,美国消费对GDP的贡献从1980年的60.8%上升到2022年第二季度的68.4%。今年前两个季度,美国家庭金融资产已经缩水 8%,预计这一轮调整下,财富效应将再一次对美国经济施压。
财富效应还通过另一条渠道影响到经济的活跃程度。随着金融市场逐步成熟,企业购并往往会借助双方企业股权置换得以完成。牛市时,企业购并活跃,熊市时,此类活动降低。2021年,美国上市公司购并活动比上一年增加了99%,达到创纪录的2.6万亿美元,很大程度也是得益于疫情后刺激政策带来的股价攀升。进入2022年上半年,在美联储紧缩政策下,股市由牛转熊,购并市场也开始降温。今年上半年,美国购并交易额比去年同期下降了29%。
脆弱的金融交易
金融市场固有的脆弱性挤压了美联储的政策空间,这是联储看跌期权(FedPut)的根本原因。四十年来,美国庞大而高度复杂的金融市场容纳了各种投资者和投机者。这里有传统的、秉承长期主义的现金投资者,有利用大数据专注挖掘资产价格和各种变量关系的量化投资者,有跨境、跨资产、跨币种的套利者,也有利用各种金融工具,为增厚收益不惜借力杠杆的投资者。这些投资人有着自己的风险收益偏好,受到各类政府部门的监管,且拥有各自不同的对冲风格。
需要提醒的是,仅在本轮紧缩政策之前,全球面临的还是一度顽固不化的通缩威胁。欧洲和日本央行纷纷实施了负利率政策,而全球的超低利率则从2008年8月到2022年3月持续了十三年之久。到此次全球央行普遍升息之前,全球负利率市场规模高达17万亿美元。投资人在这个环境下决定其资产配置、交易策略和对冲方式。
眼下,收益率曲线倒挂加深,美国10年国债与2年国债收益率差已达到-0.47%,和上两次经济衰退比,低于 2006年-0.16%的低点,但接近2000年8月-0.49%的水平,预示经济下行在即。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超过4%的水平,至少是年初的2.5倍。这意味着,给定相应的久期,投资人的损失已高达到10%-20%。目前,美国投机性期权投资净值已达到2008年金融危机时的水平,但衡量市场恐慌的VIX指数远没有达到2008年时的高位,甚至也远没有达到2020疫情暴发后的水平。
但是,金融错位(dislocations)已经在发生。历史上,每当美联储紧缩时,金融市场难免不出现大的事件。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亚洲新兴国家通过资本项下的资金流入弥补经常账户下的逆差,以求得国际收支的平衡。然而,1994年美联储开始加息,原本这些国家的资本流入变为资本流出,在“钉住汇率”的安排下,央行不得不出售稀缺的外储来平抑本币贬值的压力,终因美元储备不足而致使货币锐贬,金融资产大跌,一场危机就这样酿成了。
有趣的是,那些在特定环境下制定的、看似无懈可击的交易策略,往往因政策突变而“腹背受敌”。1998年,LTCM基金因俄债违约,其本来做空(预期风险溢价收窄而获利)的、高流动性的俄债风险溢价大幅走阔;而其做多(预期升值而获利)的、缺乏流动性的新兴国家资产则大幅下跌,多空两头同时大亏,最终,美联储不得不出面救市。2008-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原本看似完美的负基点交易(negative basis trade),由于信用风险溢价上升和交易对手风险大幅增高,再次出现了多空两头同时损失的情况。最近,英国养老金的爆雷提供了又一个典型案例,原本为满足负债端需求的、主动做空的短期利率衍生品,以及做多的、长端的国债,在利率快速攀升下,由之前的双赢变成了双损。问题是,诸如此类的金融交易还有哪些?又在何处藏匿?如美联储继续升息,此类交易会不会出现大规模崩盘的情况并引发系统性危机?而此时,联储的紧缩恐怕要被迫中断,甚至掉头。
下一个危险:欧洲还是日本?
美联储的这一轮紧缩推高了美元指数,大批国家的货币对美元纷纷贬值,通过贸易机制(进口成本增加)和资本流动机制(外债偿还负担增大)已经使一些国家不堪重压,如斯里兰卡已经破产,还有一些国家出现美元外债违约已不可避免。
另一方面,聚焦欧洲和日本为下一个风险点不是没有原因的。就在本次紧缩周期前,欧洲和日本还在应对通缩,且都在实施负利率政策。即便眼下,日本仍然处在应对通缩的努力当中。日本银行(央行)通过“控制收益率曲线”,将10年国债收益率控制在低值,而二年期短期利率仍为负值。随着美国国债收益率的升高,日元贬值成为不可避免的政策出口。前不久,美元兑日元已到了1:150日元左右,比年初大幅贬值30%以上。这样一个后果,使素有投资海外资产习惯的日本国民进一步增加了投资海外的愿望,反过来又推动了日元的持续贬值。不止是日本国民,同样的交易也吸引了机构投资人。目前,富有传统的日元利差交易(carry trade)正在回头,即卖出日元买入美元,然后投资到美国的资产上以获取利差。预期这个过程至少会持续到因日元贬值,进口成本上升,从而日本国内通胀抬头(目前已经达到1%)。如果这一切如期发生,预计日本银行随后将改弦更张,加入到美国领导的加息行列。届时,日元会回升,利差交易有可能戛然而止,动作迟缓的投资人很可能出现巨额损失并引发一波危机。需要说明,日本政府的赤字主要由国内举债弥补,日元贬值不大会像当年拉丁美洲那样造成日本债务危机。
相比之下,欧洲可能更加危险。欧元和英镑今年以来对美元分别贬值了14%和17%。由于俄乌冲突,欧洲正在经历严重的能源危机和通货膨胀。如果暂时撇开欧洲脆弱的实体经济,欧洲最大的软肋可能是17万亿负利率债券的大批欧洲投资者们,他们面对升息将如何应对。
负利率投资者仍有可能获利。一是未来更大的负利率会导致债券升值,从而导致投资人的资本利得大于利息损失;二是通过汇率变动在不同国家货币中转换,靠币值的升值获取收益,或通过货币衍生品获益。这是因为负利率地区物价往往呈下降趋势,该国货币相对其他国家往往会升值。然而,在利率(突然)大幅上升的情况下,(负利率)债券会贬值;而随着美国利率上升和欧元贬值,这正是目前负利率债券投资人面临的巨大威胁,而其风险的爆发,是不可能不影响到美联储政策的。
结语
治愈通货膨胀必定要付出代价,其代价要么是美国经济放缓、失业增加,要么是美国之外的经济体受挫,某种危机被触发;或者二者兼而有之。过去四十年,金融市场的高度发展以及美元的多重功能,使美联储的政策空间有所减小。尤其是此前超低利率下推出的投资策略,可能是阻碍美联储持续紧缩的最大黑马。美联储恐怕乐见美国经济放缓在先,更不希望其政策率先触发大规模的金融动荡,甚至是金融危机。然而,对于美联储甚至美国政府来说,更具挑战的是在地缘政治不断升温的情况下国际间政策协调的搁浅。1985年签署的广场协议,就是当时世界主要经济体推动美元贬值,缓解世界经济困境的一次努力。而这样的努力,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显得异常渺茫。目前,美联储的升息和QT都在进行。升息尚有余地,QT 按计划正有条不紊推进。可以想象,此时美联储必定在评估加息的滞后效应,以及升息与QT的复合效应,以避免政策过度。同时,美联储也一定在考虑必须兼顾的各种始料不及的情景。这一次,美国经济无论从就业,还是公司利润,都表现出不同以往的韧性,特别是美国公司税后利润占GDP比重创二战以来的新高。这样看,美联储的紧缩政策暂时还不会收手,直到通胀走低,或(不)可预知的重大事件发生。
(文章来源:新华财经)
疫情后经济刺激下的需求增加、源于地缘冲突的大宗商品价格上升、疫情管控下全球供应链中断是本轮通胀的主要原因。然而,紧缩的货币政策基本无力影响后两个因素。在地缘政治冲突旷日持久,全球供应链调整尚需时日的情况下,美联储的紧缩政策,不得不在抑制需求方面承受重中之重。
值得注意的是,美联储加息的步伐似乎已碰到了瓶颈。美元作为交换中介(交易)和价值贮藏(投融资)的双重功能,以及作为国内货币政策标的与国际储备和结算货币的双重角色,正使美联储的政策空间在今天被空前的压缩。由于金融市场的发展,美联储在试图对实体经济施加影响时,不得不考虑随之而来的金融市场稳定性问题;而在应对国内经济周期的同时,也不得不顾及对全球其他经济体的影响。考虑到美国货币政策的溢出和溢进效应,以及这些效应的相互作用,事实上,在过去30年里,美联储并未有过针对某一政策目标而义无反顾的决策环境。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格林斯潘看跌期权(GreenspanPut),2008-2009年金融危机时的伯南克看跌期权(BernankePut),以及后来的耶伦看跌期权(YellenPut),都是美联储政策归宿的明证。这里,所谓看跌期权是借用金融术语,利用看跌期权在金融资产下跌时赢利的特性,来形容联储的政策本质。更直白地说,这些政策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在实现政策目标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地顾及金融市场的过度反应(下跌),以及国际经济的现实环境。
相比之前的升息周期,本轮的升息或许让美联储更加进退维谷。眼下,从美国内部来看,一边是过热和韧性十足的国内实体经济;另一边则是长期超低利率下催生出的市值过高的金融资产。从全球经济来看,一边是处于相对强劲的美国经济;另一边则是脆弱的欧洲经济和放缓的其他地区经济。针对前者引发的通货膨胀,美联储必须果断出手,把通胀抑制在低位;但如果美国利率上升过快且幅度过大,则可能引发国内金融市场动荡,甚至触发国际金融危机。1980年初的升息,引发了拉丁美洲债务危机;1994年的升息,导致了1997年的亚洲经济危机和随后的俄债危机。如果不出意外,在这一轮抑制通胀的政策博弈中,鲍威尔看跌期权可能要呼之欲出了。
金融市场空前发展
美国战后大约发生过六次显著的通货膨胀,类似本轮这样高通胀率的情景发生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但与上次不同,过去四十年,美国资本市场伴随经济的成长,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发展。1980年,美国股市的资本化规模不到GDP的50%,而2020年已高达GDP的194%,按美元计算增长了27 倍。与此同时,美国债券市场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仅以国债为例,美国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从1980年的31.3%上升到了2022年上半年的121.07%,为 28倍。过去四十年,国际贸易的增长加大了对美元的需求。据WTO的数据,全球2020年的贸易总额为1980年的5.1 倍,其中,约一半用美元结算。在跨国资本流动方面,仅仅在过去十年,外国投资人持有的美国金融资产就从44500亿美元增加到65364亿美元,增幅达47%。
这段时间,美元虽在国际贸易和跨境资本流动中的比重有所下降,但仍然占据着最主要的地位。目前,美元约占世界官方储备货币的60%,占国际贸易结算约50%。在跨境贷款和跨境金融证券中,美元至少占40%。在外汇交易中,近90%以美元结算。即便是通过SWIFT系统的支付,美元的比重也有40%之多。
不仅在规模上,金融市场的深化也加大了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渗透。金融市场中不断涌现的金融创新,使投资人拥有了更多收益增厚和风险管理的手段,也使融资人获得了更加低廉的多元化的资金。金融产品甚至可以帮助投资人实现风险转化、风险分割和风险重组。随着互联网技术,特别是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出现,金融在不断扩大自己的疆域,并且下沉到之前从未触及到的客户群体。金融的这些发展,从某种意义上拉动了广义利差交易的各种机会和杠杆使用的各种形式。在货币政策发生(突然)变化时,根据原来政策(如超低利率)环境,按照当时投资参数设计的各种金融交易和金融运作,骤然间便可能暴露在巨大的风险之中。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愈加复杂
高度发育的金融市场,至少从三个方面改变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并影响到其决策的空间。首先,金融市场的存在使资产变动和融资效率提升,并使其多元化;同时,金融市场赋予了资产和负债的市值属性,从而改变了经济实体的资产负债结构。比如,债券融资的比重增加,而股票增发会快速改善资产负债比率。通过资产负债结构,货币政策继而传导到经济实体的损益和现金流当中。之前联储的利率调整,会通过经济实体融资成本的变化对公司的经济活动施加影响,而在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面前,仅仅“盯市”就会直接改变公司的财务状况。比如,货币收缩政策可能导致负债市值下跌。此外,还可能导致用于激励员工的股票期权等金融资产的价值发生变化。由于升息,债券市值下跌,通过对自身发行债券的低价赎回,发行人会产生投资收益,从而抵消升息对实体的影响。
升息还可能直接影响到公司的融资活动,特别是用金融资产作质押的融资。当利率上升,这些资产市值发生下跌时,贷款机构会要求借款人补充质押品,否则质押品将被减仓以用来还债,但减仓又会导致质押品市值的进一步缩水,引发更大规模的减仓,形成恶性循环,最终打击经济实体的经营活动。那些使用金融衍生品对冲经营风险的实体,升息往往会使对冲出现错位,产生新的风险敞口。此外,依赖直接融资的经济实体会发现,在利率攀升的环境下,发行人二级市场上股债流动性可能锐减,发行市场对发行人甚至完全关闭。2009年,美国雷曼兄弟垮台,很大原因是市场对其执行交易协议能力产生置疑,致使信用风险迅速转化成流动性危机。
其次,美联储货币政策会通过财富效应对实体经济发生影响。根据欧洲央行2015年的一份报告,美国2008年次贷危机期间,住房价格和金融资产价格每下降10%,家庭消费支出便分别下降0.56%和0.9%。而当年美国标普股指从高峰下跌了51.9%,全国住房指数下降了32%。事实上,2008年美国家庭损失的财富(13.6万亿美元)超过了因失业损失的可支配收入(11万亿美元),财富效应对经济的影响甚至从“助攻”转成为“主攻”。
这种财富效应在本轮紧缩中还在强化。据美联储统计,美国家庭及非盈利组织持有的金融资产,从1980年底的7.36万亿美元上升到2021年底117.9万亿美元,四十一年间增加了15倍。同一时期,非金融资产和金融资产的比例则从0.6:1.0下降到0.43:1.0.与此同时,美国消费对GDP的贡献从1980年的60.8%上升到2022年第二季度的68.4%。今年前两个季度,美国家庭金融资产已经缩水 8%,预计这一轮调整下,财富效应将再一次对美国经济施压。
财富效应还通过另一条渠道影响到经济的活跃程度。随着金融市场逐步成熟,企业购并往往会借助双方企业股权置换得以完成。牛市时,企业购并活跃,熊市时,此类活动降低。2021年,美国上市公司购并活动比上一年增加了99%,达到创纪录的2.6万亿美元,很大程度也是得益于疫情后刺激政策带来的股价攀升。进入2022年上半年,在美联储紧缩政策下,股市由牛转熊,购并市场也开始降温。今年上半年,美国购并交易额比去年同期下降了29%。
脆弱的金融交易
金融市场固有的脆弱性挤压了美联储的政策空间,这是联储看跌期权(FedPut)的根本原因。四十年来,美国庞大而高度复杂的金融市场容纳了各种投资者和投机者。这里有传统的、秉承长期主义的现金投资者,有利用大数据专注挖掘资产价格和各种变量关系的量化投资者,有跨境、跨资产、跨币种的套利者,也有利用各种金融工具,为增厚收益不惜借力杠杆的投资者。这些投资人有着自己的风险收益偏好,受到各类政府部门的监管,且拥有各自不同的对冲风格。
需要提醒的是,仅在本轮紧缩政策之前,全球面临的还是一度顽固不化的通缩威胁。欧洲和日本央行纷纷实施了负利率政策,而全球的超低利率则从2008年8月到2022年3月持续了十三年之久。到此次全球央行普遍升息之前,全球负利率市场规模高达17万亿美元。投资人在这个环境下决定其资产配置、交易策略和对冲方式。
眼下,收益率曲线倒挂加深,美国10年国债与2年国债收益率差已达到-0.47%,和上两次经济衰退比,低于 2006年-0.16%的低点,但接近2000年8月-0.49%的水平,预示经济下行在即。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超过4%的水平,至少是年初的2.5倍。这意味着,给定相应的久期,投资人的损失已高达到10%-20%。目前,美国投机性期权投资净值已达到2008年金融危机时的水平,但衡量市场恐慌的VIX指数远没有达到2008年时的高位,甚至也远没有达到2020疫情暴发后的水平。
但是,金融错位(dislocations)已经在发生。历史上,每当美联储紧缩时,金融市场难免不出现大的事件。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亚洲新兴国家通过资本项下的资金流入弥补经常账户下的逆差,以求得国际收支的平衡。然而,1994年美联储开始加息,原本这些国家的资本流入变为资本流出,在“钉住汇率”的安排下,央行不得不出售稀缺的外储来平抑本币贬值的压力,终因美元储备不足而致使货币锐贬,金融资产大跌,一场危机就这样酿成了。
有趣的是,那些在特定环境下制定的、看似无懈可击的交易策略,往往因政策突变而“腹背受敌”。1998年,LTCM基金因俄债违约,其本来做空(预期风险溢价收窄而获利)的、高流动性的俄债风险溢价大幅走阔;而其做多(预期升值而获利)的、缺乏流动性的新兴国家资产则大幅下跌,多空两头同时大亏,最终,美联储不得不出面救市。2008-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原本看似完美的负基点交易(negative basis trade),由于信用风险溢价上升和交易对手风险大幅增高,再次出现了多空两头同时损失的情况。最近,英国养老金的爆雷提供了又一个典型案例,原本为满足负债端需求的、主动做空的短期利率衍生品,以及做多的、长端的国债,在利率快速攀升下,由之前的双赢变成了双损。问题是,诸如此类的金融交易还有哪些?又在何处藏匿?如美联储继续升息,此类交易会不会出现大规模崩盘的情况并引发系统性危机?而此时,联储的紧缩恐怕要被迫中断,甚至掉头。
下一个危险:欧洲还是日本?
美联储的这一轮紧缩推高了美元指数,大批国家的货币对美元纷纷贬值,通过贸易机制(进口成本增加)和资本流动机制(外债偿还负担增大)已经使一些国家不堪重压,如斯里兰卡已经破产,还有一些国家出现美元外债违约已不可避免。
另一方面,聚焦欧洲和日本为下一个风险点不是没有原因的。就在本次紧缩周期前,欧洲和日本还在应对通缩,且都在实施负利率政策。即便眼下,日本仍然处在应对通缩的努力当中。日本银行(央行)通过“控制收益率曲线”,将10年国债收益率控制在低值,而二年期短期利率仍为负值。随着美国国债收益率的升高,日元贬值成为不可避免的政策出口。前不久,美元兑日元已到了1:150日元左右,比年初大幅贬值30%以上。这样一个后果,使素有投资海外资产习惯的日本国民进一步增加了投资海外的愿望,反过来又推动了日元的持续贬值。不止是日本国民,同样的交易也吸引了机构投资人。目前,富有传统的日元利差交易(carry trade)正在回头,即卖出日元买入美元,然后投资到美国的资产上以获取利差。预期这个过程至少会持续到因日元贬值,进口成本上升,从而日本国内通胀抬头(目前已经达到1%)。如果这一切如期发生,预计日本银行随后将改弦更张,加入到美国领导的加息行列。届时,日元会回升,利差交易有可能戛然而止,动作迟缓的投资人很可能出现巨额损失并引发一波危机。需要说明,日本政府的赤字主要由国内举债弥补,日元贬值不大会像当年拉丁美洲那样造成日本债务危机。
相比之下,欧洲可能更加危险。欧元和英镑今年以来对美元分别贬值了14%和17%。由于俄乌冲突,欧洲正在经历严重的能源危机和通货膨胀。如果暂时撇开欧洲脆弱的实体经济,欧洲最大的软肋可能是17万亿负利率债券的大批欧洲投资者们,他们面对升息将如何应对。
负利率投资者仍有可能获利。一是未来更大的负利率会导致债券升值,从而导致投资人的资本利得大于利息损失;二是通过汇率变动在不同国家货币中转换,靠币值的升值获取收益,或通过货币衍生品获益。这是因为负利率地区物价往往呈下降趋势,该国货币相对其他国家往往会升值。然而,在利率(突然)大幅上升的情况下,(负利率)债券会贬值;而随着美国利率上升和欧元贬值,这正是目前负利率债券投资人面临的巨大威胁,而其风险的爆发,是不可能不影响到美联储政策的。
结语
治愈通货膨胀必定要付出代价,其代价要么是美国经济放缓、失业增加,要么是美国之外的经济体受挫,某种危机被触发;或者二者兼而有之。过去四十年,金融市场的高度发展以及美元的多重功能,使美联储的政策空间有所减小。尤其是此前超低利率下推出的投资策略,可能是阻碍美联储持续紧缩的最大黑马。美联储恐怕乐见美国经济放缓在先,更不希望其政策率先触发大规模的金融动荡,甚至是金融危机。然而,对于美联储甚至美国政府来说,更具挑战的是在地缘政治不断升温的情况下国际间政策协调的搁浅。1985年签署的广场协议,就是当时世界主要经济体推动美元贬值,缓解世界经济困境的一次努力。而这样的努力,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显得异常渺茫。目前,美联储的升息和QT都在进行。升息尚有余地,QT 按计划正有条不紊推进。可以想象,此时美联储必定在评估加息的滞后效应,以及升息与QT的复合效应,以避免政策过度。同时,美联储也一定在考虑必须兼顾的各种始料不及的情景。这一次,美国经济无论从就业,还是公司利润,都表现出不同以往的韧性,特别是美国公司税后利润占GDP比重创二战以来的新高。这样看,美联储的紧缩政策暂时还不会收手,直到通胀走低,或(不)可预知的重大事件发生。
(文章来源:新华财经)
免责申明:
本站部分内容转载自国内知名媒体,如有侵权请联系客服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