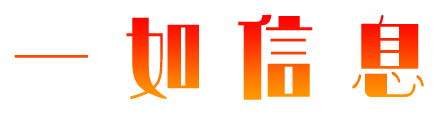长三角人郑永年
最新信息
长三角人郑永年
2023-07-31 10:58:00
“我是宁波人。”当听到圆通速递的创始人来自浙江桐庐后,郑永年也忍不住跟了这么一句。“宁波人”这个词的发音,用的是正宗宁波腔。
上周末,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郑永年受邀在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调研,为7月31日举行的2023年示范区开发者大会主旨演讲作准备,圆通速递总部是第一个考察点。
虽然早在1990年就远赴美国留学,之后又在新加坡工作多年,但郑永年似乎没有身份认同上的困惑。他不仅一直保留着中国国籍,2017年还把户口迁回老家浙江宁波余姚郑洋村。“我是中国人,是浙江人、宁波人、余姚人。”想了想,郑永年又说,“按照传统,我的称呼应该是‘余姚郑永年’,对不对?”
现在,站在沪苏浙的交界地上,郑永年又为自己的身份增加了一个新的定语——“我当然也是长三角人。”
每一户宁波人都有一个上海亲眷,这句话也适用于郑永年。郑永年的母亲本是上海人,因为家里生活困难,很小就被送到余姚乡下寄养。郑永年还记得,他小时候上海外婆来余姚乡下探望时的场景,“她的衣服是丝绸做的,吃东西很讲究,走起路来慢腾腾,不像农村老太太……”当时,乡里还聘请了从上海来的星期日工程师,这些人形成了郑永年对上海的最初印象。
这片水土给了郑永年一口江南口音的普通话,也给了他一个原装的“江南胃”,在上海的这两天,他流连于小笼包、小馄饨、生煎包,以至于难得的“吃多了”。
再延伸开来看,长三角是郑永年学术研究的起点和重点。上世纪90年代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读博期间,郑永年曾专门走访浙江、江苏等地,研究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21世纪初,在新加坡工作期间,他对中国和新加坡合作的苏州工业园区做长期调研评估;2020年以后,郑永年定居深圳后,对浙江的共同富裕建设进行考察;最近他又将目光对准了区域协调发展的比较研究。
对故土的留恋和常年的海外生活经历,让郑永年天然拥有了内部和外部两个视角,可以在观察和比较中保持清醒和审慎,理清区域经济发展的底层逻辑。如今再次眺望这片土地,郑永年说自己有了“新的idea”。
都是土豆
郑永年有点着急了。
离开第一个考察点,汽车刚启动,郑永年就和记者谈到他的一个焦虑点:“地方政府之间,都是土豆和土豆的关系,怎么才能打通?”
最近几次公开演讲,郑永年时不时提到“土豆”,他用土豆来比喻企业之间的关系,也比喻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区域之间的关系。土豆光溜溜的,颗颗分明,土豆茎一断,各自独立。地方政府间也是,“我们现在更加内卷了,互相招商引资,竞争很激烈。”郑永年观察到了这一变化。
“按理说,我们东部地区有制造业优势、资本优势、开放管理经验的优势,西部地区有阳光、风、土地等资源优势,劳动力也便宜,只要把这些优势组合起来,就能产生很大的发展动力,但为什么阻力就是这么大呢?”郑永年忍不住发问。
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上世纪90年代初,郑永年就注意到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显示当时中国各省之间的内部贸易占GDP的22%,低于欧洲共同体成员之间内部贸易的28%,也低于苏联时期各加盟共和国之间贸易的27%。当时,世界银行警告说,随着对外贸易的增加,以及相互贸易的相对减少,各省都产生了一种倾向,他们做出的行为都好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这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初就出现的一个现象:中国的企业喜欢跟海外的企业打交道,中国企业之间互相做生意的不多;中国的地方政府也喜欢和海外打交道,而不善于和其他地方政府打交道。而且,越是相邻的省,越是竞争激烈。
当时有些经济学家称其为一种新的经济现象——诸侯经济,他们将地方政府比作大大小小的诸侯,这些“诸侯”有自己的领地和组织,都在寻求独立的发展。这一现象在1980年代中期甚至引发了一场关于“新权威主义”的讨论,呼吁打破地方诸侯经济,建立全国统一市场。上世纪90年代,郑永年为此专门研究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变革与动力。当时,他就听说国务院批准成立了上海经济区,范围从太湖流域的10个城市不断扩大,但最终不了了之。
过去了这么多年,老问题依然存在。前几年,郑永年曾经跟一个东部省份的商务代表团去西北内地省份访问,发现两个省之间的谈判甚至比两个国家的谈判还艰难,行政阻隔非常严重。最近,又有城市邀请郑永年帮助他们规划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被他拒绝了。“不要再和隔壁城市在同一产业上竞争了,为什么不用比较优势来发展其他产业呢?”郑永年不解。
按照郑永年的理论推演,问题出在规则没有统一。“规则就是重要的生产力。”郑永年解释说,现在各个城市的税收返回体制、税收补贴标准、土地标准、劳动标准都不统一,导致在招商引资时,地方政府就是在这些方面挖空心思降低标准,恶性竞争,结果是平白增加了营商成本,谁也没有捞到实惠。
这并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行政本来就有边界。“形成统一大市场是很难的,并非一蹴而就。”郑永年回溯历史,欧洲也出现过“城堡经济”,各个城堡有自己的规则,互相不统一。解决这一问题靠的是强悍的外力。郑永年引用培根的论述,火药的发明成为荡平欧洲封建城堡的锐利武器。
打破“柏林墙”
说话间,调研的车辆行驶到了元荡湖,我们暂时从理论和历史中退出,回到现实。
傍晚时分,横跨上海江苏的元荡桥,美如丝带,水鸟时而掠过水面,空气中弥漫着清甜的湿气。桥上还有一处隐藏的沪苏分界线,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郑永年大跨一步,轻松实现“一脚跨两省”。但如若不提,似乎也没人注意到这条分界线,因为两地风景已浑然一体。
郑永年经常徒步,快步穿过这座不到700米的步行桥不在话下。相比风景,他对元荡湖的故事更感兴趣:元荡湖总面积近2万亩,1/4面积属上海青浦,3/4面积属江苏苏州吴江。以前,出于水域管理需要,防止对面的水葫芦飘过来,元荡湖根据省界线被密密匝匝的毛竹和网片分割开来,网障纵贯南北,不过,在2020年元荡桥贯通后,长约4000米的网障被清扫一空。
“这网障是一道变相的柏林墙啊。”在元荡桥上,郑永年看着以前的老照片,有感而发。照片上,曾经的元荡湖就是一片杂乱的芦苇荡,生态环境长期处于退化状态。抬头再望现在的元荡湖,犹如时光穿越,高下立判。再往下追问,拆除这道“柏林墙”,靠的是背后的机制创新。水中,两地共同聘请了一家保洁公司打捞水葫芦,权责分明;水上,执委会牵头召集各地相关部门和公司召开协调会,确立了一套跨区域共同审批的制度方案,统一标准。以此为始,这些年示范区已经推出制度创新成果112项。
“如果欧洲形成统一大市场的工具是火药,那么我们的工具就是体制机制改革,主动改革,这是我们的优势啊。”边分析,郑永年边回头叮嘱随行的研究人员,“赶紧再搜集一些资料,回去仔细研究。”
回到车上,我们继续回到刚才的理论分析中。“以前说的更多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现在要说地方和地方之间的关系,而这其中又有一个顶层设计,这点很有意思。”郑永年拍着大腿,显得很兴奋。
他所说的顶层设计是示范区创建的理事会、执委会运行机制,理事会是示范区的决策平台,执委会是理事会的执行机构,统筹协调跨省域、多主体的不同立场,引导各方朝着一体化的方向共同努力。截至目前,在京津冀的通州区与北三县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示范区以及大湾区的深圳、东莞等城市,都设立了类似“理事会+执委会”的机构,用以推进跨区域的协作。
“这是中国发展中逐渐摸索出的一个新模式。”郑永年告诉记者一个他的“新idea”:这种顶层设计,并不是简单地集权或者分权,而是给地方之间构建了一个协调机构,以帮助更好形成一种地方和地方之间的横向联系关系,“顶层设计后,地方和地方之间商量着办。”
“这是一个制度性的创新。”郑永年给出一个很高的评价,“我愿意给示范区的这些探索,打200分。”
争取饥饿感
汽车继续行驶在示范区的路上,离开正在建设中的华为上海青浦研发中心不久,两边车窗外就是乡间稻田,绿意盎然,这让郑永年想起了小时候:“以前父母亲都会说,不好好读书,以后就要‘摸六棵’。”宁波话里,“摸六棵”就是种田,通常插秧时,需要将一排六棵秧苗从左到右依次插入田中。
和当时大多数村民孩子一样,小时候,郑永年家里的生活十分清苦,“当时的感觉就是总是吃不饱,每天吃南瓜、土豆、番薯。”但回过头来看,穷则思变,正是当时的这种饥饿感,给了郑永年学习的动力,也给了中国发展的动力。经过三四十年发展,郑永年老家的村子早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民有钱了,环境变好了,但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现在是吃得太饱了”。
此前,在接受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采访时,郑永年曾提到每周有两个晚上让自己有点饥饿感。这次再提到这个话题,郑永年笑着打趣说:“现在是争取饥饿感。有的人吃太饱,走不动了,既得利益产生,新的发展动力在哪里?”
要找到新的动力,就要首先找到新的发展方向。对于这一点,郑永年看得比较清楚,最近,他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地域嵌入型的世界级经济平台。根据他的观察,地域嵌入型世界级经济平台成功案例有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和日本东京湾区。这些经济平台有一个共同点,不管本国的政治和社会发生多么大的危机,都不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全世界的优质资本、技术和高端人才仍然拼命涌进,进来以后不想跑、也跑不掉。
“我们也要形成我们的地域嵌入型世界级经济平台。”郑永年顿了顿说,“这正是长三角的发展方向。”
按照他的设想,要成为地域嵌入型世界级经济平台,必须拥有三要素。第一个要素,拥有一大批有能力进行基础科研的大学和机构;第二个要素,拥有一大批能够把基础研究转化成应用技术的企业或者机构;第三个要素,拥有足够支撑基础科研跟应用技术转化的金融支持。三大要素缺一不可。
再把视野拉回长三角。郑永年认为,长三角已经拥有了前两个要素,关键是要发展第三个要素。“我说的金融不是银行,指的是风投。”他进一步解释,从全世界近几十年的经济活动可以看出,从1到10的科技成果转化之路是高度资本密集型的,但是应用技术转化风险很大,所以才发明了风投。因为政府不能用财政来冒险,传统银行也不能拿着存款这么做,只有风投才能解决问题。
“长三角很多城市都成立了产投基金。”记者提醒。“这正是问题所在,很多都是恶性竞争。”郑永年欠了欠身子,反问道,“能不能像欧盟一样,建立一个共同的产投基金?按照比较优势进行产业分工,避免内卷?”
话题再次回到“土豆”。“不要像土豆一样,我们是要融合。这不仅仅是省与省之间要开放,企业与企业之间也要互相开放,国有企业要向民营企业开放,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也要开放……”郑永年语速越来越快,仿佛面前一幅欣欣向荣的发展画卷正在徐徐展开,“长三角可以由上层的协调机构来规划产业布局,然后集合政府、企业、社会、资本的力量,形成各种各样的统筹委员会,一块一块做,就能做好。”
“看来是要做成土豆泥才行。”记者插话。郑永年笑着点了点头,再次陷入思考。
(文章来源:上观新闻)
上周末,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郑永年受邀在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调研,为7月31日举行的2023年示范区开发者大会主旨演讲作准备,圆通速递总部是第一个考察点。
虽然早在1990年就远赴美国留学,之后又在新加坡工作多年,但郑永年似乎没有身份认同上的困惑。他不仅一直保留着中国国籍,2017年还把户口迁回老家浙江宁波余姚郑洋村。“我是中国人,是浙江人、宁波人、余姚人。”想了想,郑永年又说,“按照传统,我的称呼应该是‘余姚郑永年’,对不对?”
现在,站在沪苏浙的交界地上,郑永年又为自己的身份增加了一个新的定语——“我当然也是长三角人。”
每一户宁波人都有一个上海亲眷,这句话也适用于郑永年。郑永年的母亲本是上海人,因为家里生活困难,很小就被送到余姚乡下寄养。郑永年还记得,他小时候上海外婆来余姚乡下探望时的场景,“她的衣服是丝绸做的,吃东西很讲究,走起路来慢腾腾,不像农村老太太……”当时,乡里还聘请了从上海来的星期日工程师,这些人形成了郑永年对上海的最初印象。
这片水土给了郑永年一口江南口音的普通话,也给了他一个原装的“江南胃”,在上海的这两天,他流连于小笼包、小馄饨、生煎包,以至于难得的“吃多了”。
再延伸开来看,长三角是郑永年学术研究的起点和重点。上世纪90年代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读博期间,郑永年曾专门走访浙江、江苏等地,研究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21世纪初,在新加坡工作期间,他对中国和新加坡合作的苏州工业园区做长期调研评估;2020年以后,郑永年定居深圳后,对浙江的共同富裕建设进行考察;最近他又将目光对准了区域协调发展的比较研究。
对故土的留恋和常年的海外生活经历,让郑永年天然拥有了内部和外部两个视角,可以在观察和比较中保持清醒和审慎,理清区域经济发展的底层逻辑。如今再次眺望这片土地,郑永年说自己有了“新的idea”。
都是土豆
郑永年有点着急了。
离开第一个考察点,汽车刚启动,郑永年就和记者谈到他的一个焦虑点:“地方政府之间,都是土豆和土豆的关系,怎么才能打通?”
最近几次公开演讲,郑永年时不时提到“土豆”,他用土豆来比喻企业之间的关系,也比喻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区域之间的关系。土豆光溜溜的,颗颗分明,土豆茎一断,各自独立。地方政府间也是,“我们现在更加内卷了,互相招商引资,竞争很激烈。”郑永年观察到了这一变化。
“按理说,我们东部地区有制造业优势、资本优势、开放管理经验的优势,西部地区有阳光、风、土地等资源优势,劳动力也便宜,只要把这些优势组合起来,就能产生很大的发展动力,但为什么阻力就是这么大呢?”郑永年忍不住发问。
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上世纪90年代初,郑永年就注意到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显示当时中国各省之间的内部贸易占GDP的22%,低于欧洲共同体成员之间内部贸易的28%,也低于苏联时期各加盟共和国之间贸易的27%。当时,世界银行警告说,随着对外贸易的增加,以及相互贸易的相对减少,各省都产生了一种倾向,他们做出的行为都好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这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初就出现的一个现象:中国的企业喜欢跟海外的企业打交道,中国企业之间互相做生意的不多;中国的地方政府也喜欢和海外打交道,而不善于和其他地方政府打交道。而且,越是相邻的省,越是竞争激烈。
当时有些经济学家称其为一种新的经济现象——诸侯经济,他们将地方政府比作大大小小的诸侯,这些“诸侯”有自己的领地和组织,都在寻求独立的发展。这一现象在1980年代中期甚至引发了一场关于“新权威主义”的讨论,呼吁打破地方诸侯经济,建立全国统一市场。上世纪90年代,郑永年为此专门研究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变革与动力。当时,他就听说国务院批准成立了上海经济区,范围从太湖流域的10个城市不断扩大,但最终不了了之。
过去了这么多年,老问题依然存在。前几年,郑永年曾经跟一个东部省份的商务代表团去西北内地省份访问,发现两个省之间的谈判甚至比两个国家的谈判还艰难,行政阻隔非常严重。最近,又有城市邀请郑永年帮助他们规划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被他拒绝了。“不要再和隔壁城市在同一产业上竞争了,为什么不用比较优势来发展其他产业呢?”郑永年不解。
按照郑永年的理论推演,问题出在规则没有统一。“规则就是重要的生产力。”郑永年解释说,现在各个城市的税收返回体制、税收补贴标准、土地标准、劳动标准都不统一,导致在招商引资时,地方政府就是在这些方面挖空心思降低标准,恶性竞争,结果是平白增加了营商成本,谁也没有捞到实惠。
这并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行政本来就有边界。“形成统一大市场是很难的,并非一蹴而就。”郑永年回溯历史,欧洲也出现过“城堡经济”,各个城堡有自己的规则,互相不统一。解决这一问题靠的是强悍的外力。郑永年引用培根的论述,火药的发明成为荡平欧洲封建城堡的锐利武器。
打破“柏林墙”
说话间,调研的车辆行驶到了元荡湖,我们暂时从理论和历史中退出,回到现实。
傍晚时分,横跨上海江苏的元荡桥,美如丝带,水鸟时而掠过水面,空气中弥漫着清甜的湿气。桥上还有一处隐藏的沪苏分界线,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郑永年大跨一步,轻松实现“一脚跨两省”。但如若不提,似乎也没人注意到这条分界线,因为两地风景已浑然一体。
郑永年经常徒步,快步穿过这座不到700米的步行桥不在话下。相比风景,他对元荡湖的故事更感兴趣:元荡湖总面积近2万亩,1/4面积属上海青浦,3/4面积属江苏苏州吴江。以前,出于水域管理需要,防止对面的水葫芦飘过来,元荡湖根据省界线被密密匝匝的毛竹和网片分割开来,网障纵贯南北,不过,在2020年元荡桥贯通后,长约4000米的网障被清扫一空。
“这网障是一道变相的柏林墙啊。”在元荡桥上,郑永年看着以前的老照片,有感而发。照片上,曾经的元荡湖就是一片杂乱的芦苇荡,生态环境长期处于退化状态。抬头再望现在的元荡湖,犹如时光穿越,高下立判。再往下追问,拆除这道“柏林墙”,靠的是背后的机制创新。水中,两地共同聘请了一家保洁公司打捞水葫芦,权责分明;水上,执委会牵头召集各地相关部门和公司召开协调会,确立了一套跨区域共同审批的制度方案,统一标准。以此为始,这些年示范区已经推出制度创新成果112项。
“如果欧洲形成统一大市场的工具是火药,那么我们的工具就是体制机制改革,主动改革,这是我们的优势啊。”边分析,郑永年边回头叮嘱随行的研究人员,“赶紧再搜集一些资料,回去仔细研究。”
回到车上,我们继续回到刚才的理论分析中。“以前说的更多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现在要说地方和地方之间的关系,而这其中又有一个顶层设计,这点很有意思。”郑永年拍着大腿,显得很兴奋。
他所说的顶层设计是示范区创建的理事会、执委会运行机制,理事会是示范区的决策平台,执委会是理事会的执行机构,统筹协调跨省域、多主体的不同立场,引导各方朝着一体化的方向共同努力。截至目前,在京津冀的通州区与北三县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示范区以及大湾区的深圳、东莞等城市,都设立了类似“理事会+执委会”的机构,用以推进跨区域的协作。
“这是中国发展中逐渐摸索出的一个新模式。”郑永年告诉记者一个他的“新idea”:这种顶层设计,并不是简单地集权或者分权,而是给地方之间构建了一个协调机构,以帮助更好形成一种地方和地方之间的横向联系关系,“顶层设计后,地方和地方之间商量着办。”
“这是一个制度性的创新。”郑永年给出一个很高的评价,“我愿意给示范区的这些探索,打200分。”
争取饥饿感
汽车继续行驶在示范区的路上,离开正在建设中的华为上海青浦研发中心不久,两边车窗外就是乡间稻田,绿意盎然,这让郑永年想起了小时候:“以前父母亲都会说,不好好读书,以后就要‘摸六棵’。”宁波话里,“摸六棵”就是种田,通常插秧时,需要将一排六棵秧苗从左到右依次插入田中。
和当时大多数村民孩子一样,小时候,郑永年家里的生活十分清苦,“当时的感觉就是总是吃不饱,每天吃南瓜、土豆、番薯。”但回过头来看,穷则思变,正是当时的这种饥饿感,给了郑永年学习的动力,也给了中国发展的动力。经过三四十年发展,郑永年老家的村子早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民有钱了,环境变好了,但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现在是吃得太饱了”。
此前,在接受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采访时,郑永年曾提到每周有两个晚上让自己有点饥饿感。这次再提到这个话题,郑永年笑着打趣说:“现在是争取饥饿感。有的人吃太饱,走不动了,既得利益产生,新的发展动力在哪里?”
要找到新的动力,就要首先找到新的发展方向。对于这一点,郑永年看得比较清楚,最近,他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地域嵌入型的世界级经济平台。根据他的观察,地域嵌入型世界级经济平台成功案例有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和日本东京湾区。这些经济平台有一个共同点,不管本国的政治和社会发生多么大的危机,都不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全世界的优质资本、技术和高端人才仍然拼命涌进,进来以后不想跑、也跑不掉。
“我们也要形成我们的地域嵌入型世界级经济平台。”郑永年顿了顿说,“这正是长三角的发展方向。”
按照他的设想,要成为地域嵌入型世界级经济平台,必须拥有三要素。第一个要素,拥有一大批有能力进行基础科研的大学和机构;第二个要素,拥有一大批能够把基础研究转化成应用技术的企业或者机构;第三个要素,拥有足够支撑基础科研跟应用技术转化的金融支持。三大要素缺一不可。
再把视野拉回长三角。郑永年认为,长三角已经拥有了前两个要素,关键是要发展第三个要素。“我说的金融不是银行,指的是风投。”他进一步解释,从全世界近几十年的经济活动可以看出,从1到10的科技成果转化之路是高度资本密集型的,但是应用技术转化风险很大,所以才发明了风投。因为政府不能用财政来冒险,传统银行也不能拿着存款这么做,只有风投才能解决问题。
“长三角很多城市都成立了产投基金。”记者提醒。“这正是问题所在,很多都是恶性竞争。”郑永年欠了欠身子,反问道,“能不能像欧盟一样,建立一个共同的产投基金?按照比较优势进行产业分工,避免内卷?”
话题再次回到“土豆”。“不要像土豆一样,我们是要融合。这不仅仅是省与省之间要开放,企业与企业之间也要互相开放,国有企业要向民营企业开放,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也要开放……”郑永年语速越来越快,仿佛面前一幅欣欣向荣的发展画卷正在徐徐展开,“长三角可以由上层的协调机构来规划产业布局,然后集合政府、企业、社会、资本的力量,形成各种各样的统筹委员会,一块一块做,就能做好。”
“看来是要做成土豆泥才行。”记者插话。郑永年笑着点了点头,再次陷入思考。
(文章来源:上观新闻)
免责申明:
本站部分内容转载自国内知名媒体,如有侵权请联系客服删除。